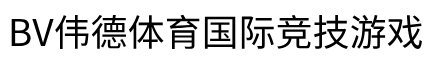
HASHKFK
欧洲杯 BetVictor Sports(伟德体育)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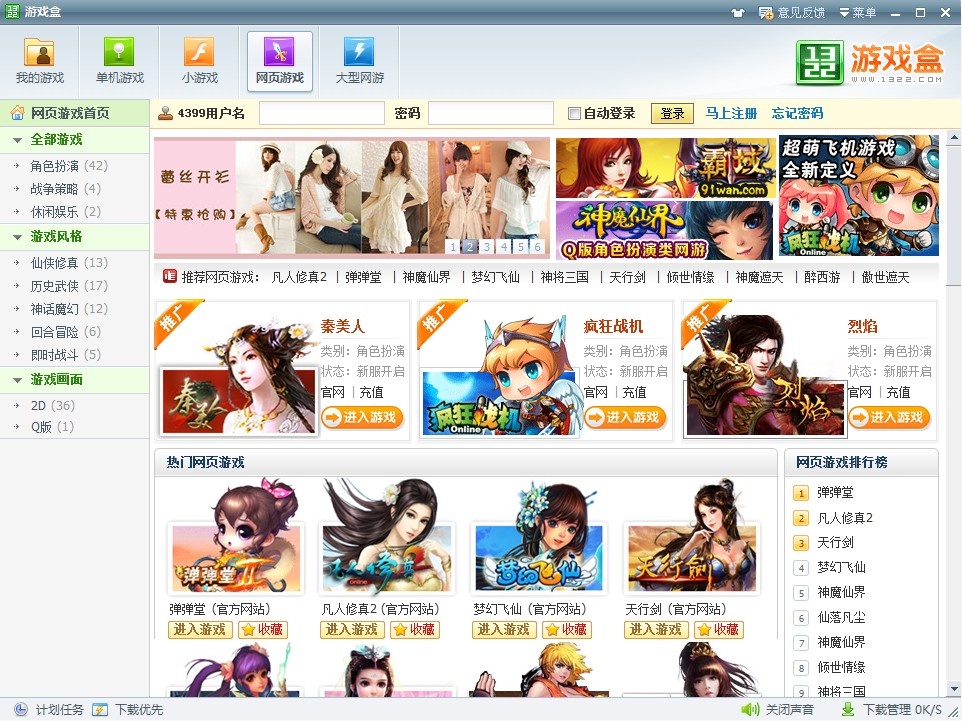
接纳移民是以色列国家建设进程中一个重要策略。19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国家一直试图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到一起。大屠杀与二战前后欧洲的环境,世界各地犹太人中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犹太人的生存境况,以及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剧变,乃是犹太移民大量涌入以色列的重要原因。犹太移民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特征造成以色列移民的独特性。自1948年到2013年,大约300万犹太移民从世界各地移民以色列。其中欧洲犹太人占2/3,东方(或亚非-犹太人)占31/3。东方犹太移民在20世纪50年代的移民(1952年到1957年)大约占东方犹太人移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比例不到百分之十。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初,85%的移民是欧洲犹太人,多数是大屠杀幸存者。但是1949年到1951年,当来自中东的伊朗、伊拉克犹太人投身于移民浪潮,情形发生了转变。从1950年5月至1951年12月,超过12万伊拉克犹太人响应以色列政府发动的“以斯拉与尼希米行动”,乘飞机抵达以色列,以色列移民人口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历史上看,伊拉克犹太人不仅认同其居住国,也认同其在居住国的身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创建犹太民族国家之时,伊拉克犹太人也在塑造自己的身份。犹太人在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许多人在流亡中来到了阿拉伯国家,客观上促进了阿拉伯世界犹太社区的繁荣。19世纪下半叶,伊拉克的犹太人更早地比,甚至比基督徒更深切地意识到掌握欧洲世俗文化和现代科学、争取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而融入更为广泛的阿拉伯世界也是犹太人世俗化过程的一个结果。自20世纪以来,以1921年建国的伊拉克为例,一些成功的犹太社区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并且融入了伊拉克的政治和文化之中。换句线年代,犹太社区的多数人把伊拉克当作自己的祖国,认为自己是伊拉克人中的一员,期待获取公民身份和民主权利,即成为真正的阿拉伯世界中的犹太人。阿拉伯犹太人是其身份,但不是唯一身份。一些伊拉克犹太人在创作中把自己当作阿拉伯犹太人,也有学者将其称作阿拉伯人,但笔者对后一说法并不认同,认为称其阿拉伯犹太人则更为确切。
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际,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伊拉克犹太人和之间的矛盾,但是,情况远比想象要复杂得多。1947年之前,犹太复国主义并未在伊拉克犹太人的身份中起到重要作用。就像在根据伊拉克裔作家埃里·阿米尔《放鸽人》(又名《别了巴格达》)改编为电影的小型发布会上,一位来自伊拉克的以色列女子所说:伊拉克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本来和平共处,但自从以色列宣布独立后,情形发生了转变。面对政府、媒体与大众的敌意,当时认为已在伊拉克扎根的犹太人,感到其经济身份与公民身份遭到破坏。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加入了,希望伊拉克政体能够改变。另一些人则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中。与此同时,巴格达的犹太领袖反对当地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犹太拉比也惧怕失去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年轻人一般热情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伊拉克犹太人的身份中包含了“伊拉克人”、“公民”、“犹太信仰中的伊拉克人”、“阿拉伯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等多重含义,具体哪种含义占据主导地位,则视使用者的社会政治地位与社会文化阶层而定。正因为此,以色列建国之后,伊拉克犹太人意义中的“犹太国复国主义者”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他们与伊拉克国家的关系开始对立起来。1950年3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允许放弃公民权的犹太人离开,但这条律法条例只保留了一年。迈克尔的《维多利亚》虽然主要叙写的是犹太人在伊拉克的生活,也曾经暗示维多利亚的儿子加入了,但只是一笔带过。相形之下,埃里·阿米尔则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更为精细的诠释。
阿米尔1937年生于巴格达,1950年随家人移民以色列,先在基布兹接受教育,后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中东历史和希伯来文学。曾为以色列总理做阿拉伯事务顾问,并一度管理以色列新移民事宜,积极参与巴以关系问题的探讨。与此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作有《替罪羔羊》(1983)、《放鸽人》(又名《别了,巴格达》)、《扫尔之爱》(1998)、《雅思敏》(2005)、《骑自行车的孩子》(2019)等长篇小说,曾经获得青年移民五十年庆典奖、墨西哥犹太文学奖、以色列总理文学奖和布伦纳奖等。
其鸿篇巨制《放鸽人》为我们展示20世纪四五十年代伊拉克犹太人风起云涌的历史。小说的大部分背景置于伊拉克巴格达。与迈克尔的《维多利亚》主要描写家庭与个人生活不同,《放鸽人》虽然从小叙述人卡比父母的日常生活写起,但注重烘托巴格达犹太人的生存环境:特务机关每天来家中搜查是否藏有武器、收发报机,以及“运动”发的希伯来语课本。“运动”即巴格达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的称呼。数百名犹太人被拖入酷刑室,被迫在军事政权的即决审判中承认有罪。整部作品的叙事背景置于犹太商人沙菲克·阿达斯(Safik Addas)被处决、伊拉克颁布犹太人移民律法(移民者首先要被取消伊拉克公民身份)到1950-51年几乎整个犹太社区逃往以色列这三年间的动荡岁月里。阿达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伊拉克犹太首富,与几位部长,甚至摄政王过从甚密。他和合作伙伴购买英国废金属,后将这些废金属运往意大利,而军事法庭则认定这些旧金属最后被运往以色列的武器加工厂。1948年8月,阿达斯遭到逮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意味深长的是,阿达斯是生意合作伙伴中唯一的犹太人,也是唯一受到惩罚的人。据作品描述,以色列建国后,新任伊拉克国防部长萨迪克·阿里-巴萨姆(Sadik al-Bassam)试图教训犹太人。阿达斯正好是天赐之物。巴士拉的一家报纸要求阿达斯捐款遭拒后,就发表文章指控阿达斯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出售武器,为以色列国家做间谍,并要就此展开调查。阿达斯本人并未意识到危险,没有及时逃离,因此在被逮捕后迅速被判处绞刑。如果把史料和文本信息叠加起来,便会看出,阿达斯事件反映出伊拉克当权者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的极端仇视;阿达斯之死,既是伊拉克仇视犹太人情绪的高峰,也标志着伊拉克犹太人生存境遇的转折。
《放鸽人》堪称伊拉克犹太人的民族叙事。尽管在伊拉克这片土地上,古代犹太人曾经创造出《巴比伦塔木德》,记述了犹太人的精神生活和宗教创造,再现了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犹太人一千年左右的生活。其后他们在那里生活了数千年,创造出丰富的文化遗产,讲犹太阿拉伯语,并已经融入了当地文化之中。20世纪初期,许多犹太人步入伊拉克上流社会,对伊拉克的文学与文化产生了影响。但是犹太国家的建立直接影响到伊拉克犹太人的生存境遇,加剧了伊拉克犹太人与伊拉克政府和当地阿拉伯居民的冲突。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的第二天,伊拉克向以色列宣战,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在政府任职的犹太人被解雇,银行家和商人不能像从前那样自由经商,年轻人不能进大学读书。
与历史进程类似,在阿米尔笔下,犹太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国家的敌人,一切发生了转变,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任何人不知道明天该发生什么。即使普通的阿拉伯人也声称要砍掉者的头颅,把犹太复国主义者送上绞架。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叙述人的叔叔希兹克尔(Hizkel)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在阿达斯之死后发表社论,称沙菲克·阿达斯审判实际上是每个犹太人都将面临的审判,类似德雷福斯事件。阿达斯能被绞死,谁会能拯救其他犹太人?很快,希兹克尔也遭到了逮捕。
这部小说描写了卡比的父亲,希兹克尔的兄弟阿布·卡比和希兹克尔的年轻妻子拉舍尔为寻找希兹克尔下落,希望其获释而做出的日益绝望的努力。卡比的父亲意识到伊拉克犹太人面临的危险,预言他们很快将被绞死,开始期待离开这座曾经居住了家族70代人的城市,去往心目中的圣地以色列。在他心目中,犹太人在以色列可以享有自尊。那里有犹太军队、犹太政府和犹太国家。于是他和弟弟与朋友一起组织青年运动,为巴勒斯坦募捐。而母亲却将此视为男人冲动的征服与冒险梦想。
就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言,犹太历史学家雷蒙德·谢德林(Raymond P. Scheindlin)曾经论述:许多中东犹太人似乎在犹太复国主义中找到了出路。换言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许多中东犹太人具有天然的感召力。原因在于,与西方犹太人相比,中东犹太人与以色列人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部分是因为他们许多人生活在离以色列更近的地方。但在这方面,伊拉克犹太人却显得比较特殊。叙述人的父亲与叔叔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并非所有的巴格达犹太人都愿意移居以色列。伊拉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很小型的运动,其成员大概只有大约两千左右的年轻人。
其次,从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流亡伊拉克的犹太人已经在巴比伦岸边安身立命。尽管古代犹太人之所以来到巴比伦是因为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但广为人知的是,当波斯大帝居鲁士结束所谓的巴比伦囚虏时期后,只有一些流亡者和后裔返回耶路撒冷。余者,施罗莫·桑德(Shlomo Sand)所说的“绝大部分人”选择日益繁荣的东方犹太文化中心,并在那里日渐繁盛。就连犹太人引为自豪的一神教也是在流散地得到系统阐述。在流散地永久安家的犹太人一直将耶路撒冷视为中心,这一事实与其宗教思想并不矛盾。在居鲁士法令颁布的若干年后,在苏拉、尼哈迪亚、帕姆贝迪塔等地由流亡者后裔创立的学堂成为犹太人完成宗教与祭祀仪式的重要场地,最后促成了《巴比伦塔木德》等犹太经典文献的诞生,对后世的犹太思想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岁月荏苒,伊拉克犹太人虽然拥有犹太拉比、犹太会堂、犹太丧葬传统,恪守犹太教和犹太习俗,平日说话也会援引圣经典故,如在形容女子之美时称之为“荆棘里的玫瑰”,美如王后以斯帖等。但本质上,多数犹太人已经被流散地同化,他们热爱这里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一员,把流亡视为犹太人的唯一出路。他们虽然不像后来一些欧洲犹太人那样皈依异教,但对新建的以色列国家没有兴趣,为此,他们甚至否定犹太文化史上具有原型色彩的亚伯拉罕迦南之旅。理由是首先不应该流亡;其次,即便流亡,也不应该选择一个遭诅咒的地方,按照《圣经》描述,吞噬其百姓之地。在这类人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住在伊拉克。还有一些伊拉克犹太人,比如希兹克尔的妻子蕾切尔与多数巴格达犹太人则期待通过与联合国分治协议妥协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平和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她未曾想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伊拉克都卷入了与新建以色列国家之间的战争。
第三,新建的以色列国家并不具备接纳与安置流散地所有犹太人的条件。一位曾经代表以色列国家与伊拉克政府进行谈判的伊拉克犹太复国主义者回忆:他曾经与负责安顿新移民的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kol)在1950年进行过一场谈话。艾希科尔说:听说一年内将会来6万(伊拉克犹太人),请告诉你的犹太好人,我们很高兴他们前来,但是让他们别急。我们眼下没有接受他们的可能性。我们甚至没有帐篷。如果他们来了,就得住在大街上。
与这种现实相呼应,在小说《放鸽人》中的放鸽人阿布·爱德华看来,希兹克尔之所以被捕,并非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破坏了对犹太人的信任”,“是一场灾难。”同时,他并不认为以色列比巴格达安全,不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取得胜利,认为那里随时会爆发一场新的战争,因为阿拉伯人也不会忘记巴勒斯坦,那里有圆顶寺和圣石。主人公父亲与放鸽人之间的争论不仅代表着巴格达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抗拒,也预示着巴勒斯坦地区未来的争端。耶路撒冷是一座神圣的古城,是犹太教和教的共同发源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封堵了阿拉伯人的朝觐之路,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伊拉克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同态度,体现出伊拉克犹太人不同的价值观念。放鸽人安于现状,倾向于留在巴格达。在巴格达,犹太人生活安逸。在土地上劳作,库尔德人为犹太人清理厕所。而到了以色列,这一切恐怕不再可能。而以主人公父亲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强调亲自耕种土地。放鸽人认为犹太人不需要土地,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认为,没有土地的民族则像没有星光的天空。在犹太历史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具有一种优越感,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放鸽人则对选民之说持怀疑态度,认为今天的安逸生活拜所赐,没有意识到犹太人迟早被伊拉克驱逐的危险。期待结束漫长的流亡,把伊拉克从内心深处连根拔除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把与同胞谈话当作人生中的一个使命。争论焦点便是如何认知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