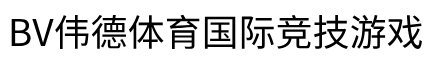
HASHKFK
欧洲杯 BetVictor Sports(伟德体育)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被誉为美国现代文学开山之父的海明威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可以说是超群的。很多著名小说家被人记住的短篇小说往往只有一两篇,如菲兹杰拉德的《重返巴比伦》,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雪莉·杰克逊的《彩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好人难寻》和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而被评论家称作名篇的海明威短篇小说多达十余篇,除了读者比较熟悉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杀手》《白象似的群山》《在异乡》《印第安人营地》和《大双心河》外,还有《我老爹》《没有被斗败的人》《雨中的猫》《士兵之家》和《桥边的老人》等等。根据1975年出版的《海明威短篇小说评论集》编辑者杰克逊·本森的粗略统计:到1968年为止,海明威的短篇共被各种短篇选集(不包括他自己的短篇集)收录了410次。
除了被收入海明威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短篇全集《49个短篇小说》里的《桥边的老人》,海明威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短篇小说被评论界谈论得相对较少。《桥边的老人》是作为记者的海明威报道保皇党撤退的电报稿。当时海明威正好欠《时尚先生》杂志下属的《视野》杂志一份小说稿件,所以他把那份电报做了几处小改动,如把三只猫改为一只,把老人的年龄从68岁改成76岁,又增加了几段对话后直接发给了《视野》。这篇小说也成为海明威生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里的最后一篇。而《在山梁下》等另外四篇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小说,海明威生前只在杂志上发表过,直到1969年才收入由他的第四任太太整理出版的《第五纵队和四个西班牙内战短篇》中。评论家们公认《在山梁下》是这四篇小说中最好的一篇。海明威在写给他的编辑马克斯·珀金斯的信中说宝琳(他的第三任妻子)认为这篇小说是他写得最好的短篇之一。
为了便于理解《在山梁下》这篇小说,先简单介绍一下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8日-1939年4月1日)发生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奏。对阵一方为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的共和政府军与人民阵线,另一方是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长枪党等右翼集团;共和政府军受到苏联和墨西哥的援助,佛朗哥国民军有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葡萄牙的支持。英法美等国(包括中国)虽然保持中立,但由民间人士组织的“国际纵队”则前往西班牙加入阵线参战。
《在山梁下》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叙述者是来前线拍摄国际纵队进攻影片的记者,当时海明威与“北美报业联盟”签约前往西班牙报道战事,他还与荷兰电影导演、第三国际行动人员尤里斯·伊文思合作拍摄反映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大地》。所以这也是海明威的真实经历。小说描述了由国际纵队主导的一场进攻战。小说以他和摄影师一起从战场撤退到山梁下开头,他们与作为预备队的西班牙士兵一起待在战壕里等待发起总攻。海明威对场景的描述简洁生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发起进攻前繁忙的后方。通过叙述者的描述读者意识到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进攻。作为进攻方的我们火力不够,“当需要四十门排炮的时候,我们却只有四门”。“(他)只有一个旅,却出乎意料地接到发起攻击的命令……这么做至少需要一个师的兵力。”小说通过“我”亲眼目睹和与西班牙士兵交谈得知的几个事件,讲述了这场不成功的进攻中那些不会被记录在案的故事。小说以“我”和摄影师“沿小路下山,去搭乘去马德里的指挥车时”,看见了那个被督战队击毙在山梁下的法国逃兵结束。
海明威描写战争的短篇大多表现战争对个人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在异乡》《你们绝不会这样》《此刻我躺下》),以及如何从战争的后遗症中康复(《大双心河》《士兵之家》)。但在《在山梁下》这篇小说里,海明威第一次探讨了战争的本质和意义。通过叙述者与作为预备队的几位西班牙士兵的对话,海明威对战争的本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关系提出拷问。在西班牙士兵眼中,现在支持西班牙政府的盟国都是曾经的侵略者,“在巴达霍斯,英国人和法国人掠夺洗劫我们,侵犯我们的妇女。”“我父亲是被古巴的北美人杀害的,他在那儿被强征入伍。”
以写硬汉著称的海明威擅长描写人们面对死亡和危机时表现出的勇气、决心和坚毅,如《没有被斗败的人》里与公牛决斗到死的斗牛士,《老人与海》里与大马林鱼搏斗了三天、最后只带回家一副大鱼骨架的老人。但在《在山梁下》这篇小说里,他却塑造了一个擅自离开前线的逃兵。那个法国士兵隶属于国际纵队,当年肯定是怀着一腔热血自愿来西班牙参战的。当认清自己的付出和牺牲毫无价值时,他毅然决然地昂首离开了战场。由于叙述者“我”曾经“身处尘土、硝烟和枪炮声中,身处受伤、死亡、对死亡的恐惧、勇敢、怯弱,以及不成功的进攻带来的失败感和荒谬之中”,所以能够理解“死于一场不成功的进攻是多么愚蠢”。小说的叙述者一直用符合新闻记者身份的客观视角观察事物,他虽然亲临战场,但并没有介入到战斗中。他一方面承认战场上督战队存在的必要(“战争中必须遵守纪律”),另一方面又被督战队的残暴(枪杀帕科和追杀法国中年逃兵)所触动,无法调和战争中“遵守纪律”和“个人的生存愿望”这一悲剧性的辩证关系。而这样的悲剧场面是不会出现在他们正在拍摄的记录战争的影片里,电影里“它们(坦克)势不可当地冲过山丘,像大船一样登上山顶,朝着我们拍摄的胜利的幻影叮叮当当地驶去”。
《在山梁下》这篇不足八千字的短篇里包括了时空上的多次转换。小说描述的是一场即将开始的进攻,这也是叙述者此行的目的:记录这次进攻。借助叙述者“我”与西班牙士兵的对话引出了帕科被督战队枪杀这一残酷的事件。小说还讲述了这场进攻失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法国的坦克指挥官为进攻壮胆喝醉了,最终因为喝得太醉而无法指挥。酒醒后他会被处决。”“他(国际纵队的指挥官)却没能遵从他自己的忠告,因为两个月后他就把命给弄丢了。”小说中充满了戏剧性的翻转:害怕战争而自残的帕科在认清自己的软弱后,却被督战队枪杀;自愿参战、最终不愿死于一场准备不足的战争的法国人,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了我方督战队的手里;告诫叙述者“别把命给弄丢了”的俄国军官自己却于两个月后丢掉了性命。作家和诗人韦恩·克瓦姆认为《在山梁下》是一个“关于作家如何写小说的小说”。克瓦姆的分析从作者“对地点的敏感”出发,这不仅是对物理场景的敏感,还包括对场景中其他人物的道德或情感位置的敏感,作者借此获得了对人性的理解。
在小说的结尾处,那个中年法国人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战场的。因为他“突然看清了一切,看清了这场进攻的无望,看清了这场进攻的愚蠢,看清了这场进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可能不是因为惧怕,而只是因为看得太清楚了”。《在山梁下》里的中年法国人与《没有被斗败的人》里的斗牛士不一样,因为斗牛士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能够战胜公牛。他与《老人与海》里的老人圣地亚哥的心理状态也不一样。因为老人面对的是必须取胜才能生存下来的战斗。而《在山梁下》里的法国士兵面临的是一个确定的失败,确信自己将“死于一场不成功的进攻”,所以他昂首退出了战场。